法正走在成都的芙蓉巷,脚下踩着半黄的落叶,听着登云履与厚厚的叶子相触发出的“嚓嚓”声,丹田下升起一股豪气,那声音,真的很好听,像是,砍头发出来的呐。
他新的办公地就在这条巷子里的一座很像样子的府地。原来的主人随着刘季玉远走南郡,带着一路的凄清,留下了当年的肃穆。
背着手在大门外仰头而视,脸上的肌肉有些抽搐,看着气派的六级青石阶,不禁回忆起,三年前,自己走上这里,还要热络地拉着门房的手,悄悄地塞上几两银子,直待里面向着他将手一勾,自己也便就提起了袍,一溜小跑地走了进去。
“咳!”
用力的咳了一声。立刻,门里就探出一颗头来,浑黄的眼睛像是发现了什么宝物一般顿时亮了。
“法大人?”门分左右,又有几颗头钻出来,变戏法似的就冒到了法正的身边,躬着身子,偏着脑袋,唯唯诺诺地说着什么,法正不想听,但他喜欢看,看他们这样诚惶诚恐地围着他,尽情地享用着这些昔日里给他颜色看的,小人们的媚态,他甚至为了进一步看看他们能谄媚摇尾到何种承度,还会在闲走时,有意无意地对着其中一副小心伺候的面孔夸赞奉迎那么一两句,果然,他就真看到,像是一群对着主人低眉顺目的犬,用脖子蹭着他的鞋,呜呜地发出媚人的声音。
“把府中官员名册调出来我看看。”他平平气坐在案前,接过厚厚的一撂的簿册。不经意地看了看,“太多了,你给我找……”
几名书吏马上把册子搬开。
“秦平、苏阶、赵戬……”法正抿着香茶,从口里幽幽地飘出几个名字。
不到一刻,那些官员的档案就被调了出来,法正微微闭了闭眼睛,将簿册上的尘土吹了吹,“他们还在这儿混饭吃么?”
“是,将军,皇叔前者颁布教令,命原有官员,仍在旧处听命。”书吏小心地说。
“哦。”法正轻轻笑了笑。“皇叔是仁爱的,啊~饭也是要给他吃的,行,你去吩咐了,他们的差事,先不要办了,在家听消息,我自有新的官吏来上任。”
“那薪俸的事……”
“嗯,两餐粮米,可以到府里来吃,记着,只许吃,不许多拿。”
法正在府里未到一天,这样的被弃置不用的官员多达数十人。一霎时,这府里的空气紧张得仿佛可以点燃,又加上天上飘了细雨,人人的心里都像是发了霉。
“法正!你不要欺人太甚了!”
果然有爆炭性子闯进府来了。法正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,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。
“啊啊啊,子琰贤弟!你还是那么风光啊,哎怎么样啊,刘将军现在还是那么信任你吧?哦对了,我竟忘了,刘将军在雒城阵亡了,唉,这人生一世,哪有那么顺心的?就像老弟你,当初威风八面的时候,求着老弟办点小事,真比求着当今陛下还难呐,你看你看,现在你不是还那么张扬嘛,这就是气节呐!”
“法孝直!别仗着你的新主子就不知天高地厚起来,你是个什么东西?站在这里哟五喝六?若是季玉公在,岂容你如此张狂!”
法正沉下脸坐下来,“听见了么?嗯?”他歪着头,伸起一根指头点着面前语无伦次的书生,“听见他在说什么?他说‘季玉公若在’,你好大的胆呐!”声音放得低沉了些,目枭鸟般盯住面前浑身打战的人,“皇叔新统益州,你竟敢煽动刘璋旧臣造反?!”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!”
“来人,来人。”法正的声音不大,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,武士进来了,向着他拱了拱手,“大人。”
“皇叔进城后有禁令,妄言煸动旧臣做乱者,怎么处置来着?”
“这……是斩罪。”
武士看看尚不知所措的文士,又看看一脸怜惜的法正,等待着示下。“带下去吧,别让我老弟受太大的罪,手脚麻利些个。”
文士显然是明白了什么,气极而泣,法正竟有些期待地等着欣赏他破口而出的恶语了。可是那武士竟然像拖着个死狗样很快就把他扯下去,好不让法孝直一阵叹息。
“法孝直心胸狭隘,公报私仇,至有人命,军师将军宜启主公,抑其威福。”
诸葛亮未动声色地摇着羽扇,望着面前微皱双眉的主簿。半晌,才轻轻问,“有人命?”
“是的。原来与他有私怨的九人,都被他以煽动造反为由,下狱诛死了。这样的话,于稳定川人之心不利。”
主簿紧盯着诸葛亮的脸,却未发现任何表情,只是羽扇摇得略缓了些,片刻,就听到很随意的一声,“嗯,知道了,先下去吧。”
有九条人命。
诸葛亮坐在车里,打起车帘看着成都街市上川流不息的人群。这是自己日夜思慕的天府之土,自己的梦想、才华、志向,都将在这片土地上绽放,怎么会,刚刚踏上来,就会有这样的事。
左将军府的大门从来没有向诸葛亮关上过,实际上,“署左将府事”的头衔让诸葛亮成了这里的半个主人。
“主公在哪里呢?”匆匆地问一个长史。
“在西暧阁。”
“哦。”诸葛亮点点头,往里走去,那长史又加了一声,“和扬武将军饮酒呢。军师也去凑凑趣。”
“哦。”仍然是这一声,脚步却明显地慢了下来。停了一会,慢慢地向西暧阁踱去。
穿过有些枯萎的藤萝架,拂开参差挡在眼前的花枝,渐渐的,西暖阁中火热的笑语带着酒气从屋里四溢而出。
“哈哈!法孝直!痛快!告诉你,孤平日最恨的,也是那起肩膀上扛个脑袋,眼睛只会向上翻的竖儒!”
“正的脾性也是过于急切了一些。”
……
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向前走,就这么一直在对扇门前立着,羽扇也停止了摇动。
“孝直,那些鼠辈有没有……尿了裤子?”
紧跟着,是两个人带着钩儿似的笑声。钩得诸葛亮的头一窝一窝的生疼。
“军师将军。”
廊子下的一个侍者躬身带笑地走了过来,“主公吩咐过,您若是来了,就请进去吧。”
犹豫着,不知道这种场和,这种话题,自己进去还有何意义。而屋里的人显然是听到了外面的声音,借着酒气高声招呼着,“孔明来了吗?怎么还不进?”
不进是不行了。诸葛亮瞬间恢复了世间无二的优雅,袖底荡着清风,羽扇摇得潇洒,面带微笑地走了进去。
屋里的酒席已吃得一片狼藉,两张案子紧对着,青铜酒器里的酒将将告磬,法正红扑扑的一张酒脸,笑得盛开着菊丝;刘玄德仰靠在檀木扶手上,敞着胸衣,满脸是玩味的笑容。
“主公,孝直。”很随意地行礼,为了不使自己与这两人显得过于格格不入。
法正直起身拱了拱手,刘备只是摆着手,“来来,坐下坐下,一起喝几杯。”说着招呼侍者重上酒席。
诸葛亮躬身笑道,“不了,少时还有公务要办,主公和孝直难得有兴致,亮就不打扰了。”
“有什么重要的事吗?”刘备探着身子。
“也没什么,过两天再说也无妨。”诸葛亮的脸上始终是云淡风清。
“军师将军既然遇上了,也陪主公少饮几杯。”法正仍殷勤地让着。刘备却用手指叩着案子点着头笑着说,“让孔明去吧,有他在儿,咱们就喝不痛快了呢。”法正和诸葛亮都发出呵呵地礼貌性地笑声。
诸葛亮施礼而去,法正起身相送,待回过头来时,却看见刘备的面上半含着笑意,目光幽幽地描绘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出神。
“主公,”法正坐下来重为刘备满上一杯。小心地问道,“军师将军,总是这样行止如仪,稳重端庄么?”
刘备的目光仍未收回,手却擎起酒杯来一饮而尽,复从案上搛起一箸鹿脯在口中嚼着,微眯起眼睛,慢慢地望向法正,笑容荡在脸上,神秘地向他竖起手掌,压低了声音说,“床帷里不是的。”
盯住刘备的眼睛看了半天,法正扑地笑了出来,刘备也笑得垂下头用手托着额。
“主公啊,你竟连人家的闺房之事都晓得,真个神通广大呀!我可听说,军师将军的夫人乃一代贤妇,这种玩笑可不要让军师将军知道了才好……”
“她哪里见过。”刘备的舌头有些大,话音里带着些许的愤懑,抬头死瞪着法正。
“啊?”
法孝直被刘备的话弄得不知该说什么好,刘备却忽然间意识到什么似的,不知是酒性发做还是别的原因,那脸竟红得如晚秋的红叶一般,“呵呵,呵,谁……谁都没见过……”
“主公今天酒厚了。”法正欠身扶住了歪歪倒倒的刘玄德,不觉自己也有些摇晃,点手叫过了侍从,搀了刘备往寝处去,自己摇着步子走到院中,迎着风打了几个酒嗝,觉得头有些疼,命人备了车马,也回了自己的府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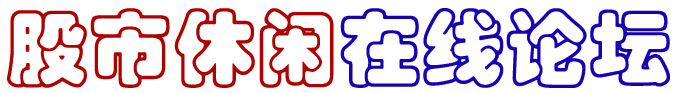

 ,给梦姐献香茗
,给梦姐献香茗 ,给梦姐送礼物
,给梦姐送礼物 ,给梦姐送花
,给梦姐送花 ,这样梦姐有灵感了没?
,这样梦姐有灵感了没?
 ……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