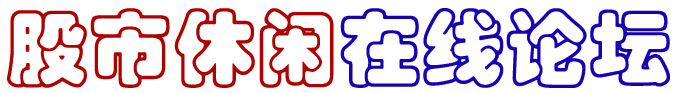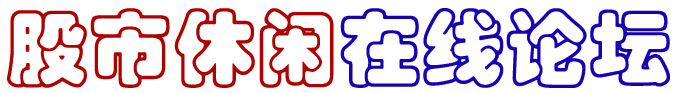|
“或许下次见面,就是在战场了,苟富贵,莫相忘啊。”收拾行李离开时,一个老儒生用浑浊的眼睛盯住我看,我待要回答些什么时,他竟然把目一合,不再理我。
走出寨门的时候,我不禁停住了脚步。真的要别过了么?
神威凛凛的关将军,跨一匹赤兔追风,但每见了我都会停下步子,拱手叫一声“先生”;粗豪直率的三将军,营中少不了他的大嗓门,他也曾拉着不相识的我灌进三大杯酒,之后亲热地狠狠拍着我的背:“年轻人,够意思!”;安静忠厚的子龙总是一身白衣,那次与我投壶作戏,输了的我还要再饮,他见我已微醺,便笑按了我的手,一指瑶琴道,“先生以曲代之罢”;简先生是个相当洒脱不羁的人,我至今记得他坦腹笑言“孔明的学问,在我之上哪”。还有,我的……主公,刘备刘皇叔,永远带着温和的、亲切的神情,让人不知不觉想要接近。
我心中生出些留恋来,刘备是个随和的人,将军幕宾们之间也是多年的交情,营中的气氛随意而亲厚,让我很舒服。哎,诸葛孔明就要和这些人错身而过了,下次见面,或许就在战场。
诸葛孔明为什么要走呢?诸葛孔明到底要什么?
我闭了双目,耳边是呼啸风声。
“外面风大,先生注意身体。有什么需要尽管向刘备开口”,那是第一次,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触膝夜谈吧?我把他赠我的披风留下了,平平整整地叠好,放在榻上。
诸葛孔明需要的,不是你荫蔽下的一方天空;
诸葛孔明要和你站在同样的高处,指点风云变幻。
刘玄德,在你的温和眼神中,孔明找不到想要的那份倚重与理解,找不到共同创业的激情,所以孔明要走了。初识那天你拉着我的手说,“来,孔明,跟着我干一番事业。”当时我多么想说,“孔明要的,不是你的事业,而是我们的事业。”
刘玄德你也许还不懂,诸葛孔明是个骄傲的,自大的人,天下,不仅仅是你的梦想,也是诸葛孔明的梦想。
离开的时候,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中,我随即重重敲了敲自己的脑袋。
这里,或许还会回来……
“走了?”听儒生说诸葛亮已经离开,虽然已经有所准备,但是还是很失望。我皱了眉头,随眼就扫到榻上叠得平平整整的一领披风。这年轻人,非泛泛之辈也。
扫了窄小的榻一眼,随口问道:“他一直睡这里?”
“是的是的,不过他每天晚上,回来得挺晚的,也不知道……”儒生凑在我身旁说,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。
想到他这么一个高个子,和别人挤在榻上,肯定挺别扭的吧。回来得晚……一个身影闪过脑海,我心中一跳。
诸葛亮没有留下话说他要到哪里去,也许是,不再回来了吧?我拿起了那领披风,挥挥手让就要围上来聒噪的幕宾们散去。
回得营来,吩咐了简雍登记流民的事情,简雍连呼妙计啊妙计何人所献必当重用云云,我不置可否地笑一笑,心里有几分怅然。又命人多辟了几间屋舍让文士们住得宽敞一些,不久便有络绎而来感恩颂德的,可惜都不是我想见到的人。
人都散了,帐中空荡荡的,我在灯下又摊开了那几纸策论,心中的怅然又添几分。
窗外秋风流转,星河灿烂。一个年轻儒生,羽扇纶巾,眼角眉梢含着温雅的笑容,掀帘而入,沉默地望了我许久,便转身离去了。我正要起身去追,却豁然从梦中醒来。梦中那书生落寞的眼睛,像极了西天的启明。
回到隆中已经五天。那天月英看到我一身风尘,推开草庐的竹栅门时,眼中竟然不起波澜。“回来啦?”笑着接过夫君手中依旧简单的行囊,忙着吩咐童儿烧水备茶,就像我每一次外游归来。
院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,只是疏疏的篱落间,瓜蔓已然攀高不少,去时烂漫的黄花,已经结出小小青果。诸葛孔明离去只有一个月罢,本以为此一去君臣际会共逐功业,若要回得家乡,只能在梦中。却不想路途多舛,才不得尽志不得展,半路默然归来。依旧的风过翠竹鸟声婉转,依旧的落曰斜照牧歌悠扬,依旧的白衣书生一身萧索。
看着月英忙碌的身影进进出出,我顿时为自己的清闲感到悲哀,几曰来极力压抑的惆怅霎时涌上心头。曾经用冷彻的理智分析了自己在刘军中的位置,得出了必须离开的结论,我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,可是为什么心中却依旧五味杂陈?
“天地反复兮火欲镞,大厦将甭兮一木难扶,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,名主求贤兮却不知吾。”月光下的溪水浮起夜雾,盛托了我缓缓的歌声送向远方。我知道月英无声立在我身后,我知道她的眼神潮湿忧伤。
“天地反复兮火欲镞,大厦将甭兮一木难扶,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,名主求贤兮却不知吾……”喧嚣的市集上,清朗的歌声让人心神一震。我急唤了子龙,循着那歌声疾步走去。
一个穿着麻布长袍的男子,怀中抱了长剑,斜卧在一块青石上晒着太阳唱歌,他叫徐庶徐元直。从第一次看到他起,我就肯定我们必会极之投契。
跟着我回到军中,元直大着嗓门问我:“孔明那小子在吗?”
孔明?好生熟悉的名字。
看到我的沉默,元直不禁露出奇怪的神色。
“怎么?诸葛亮没有到你这里来?好小子,诳我呢……”
“哦,是他么。走了。前几天,不声不响就走了。元直认识他?快把他喊回来吧”
我一口气说完,语气中的急切让元直有些意外。他眯缝了眼睛笑嘻嘻打量我半天才说,“岂止认识,还是极好的朋友呢。我常常到他的家蹭饭,哈,弟妇的手艺真是……”元直见我急切,便故意把话题往外拉。
我没好气地瞪他一眼,“那元直明天就去把他请回来。就说,恩,我对他的策论很满意,回来,恩,必当重用!”
“主公哪主公,你还不了解他的脾气呢,怪不得他要走。此人,只可就见,不可屈致,而且……”元直又是笑,神色越发悠闲.
“而且什么?”
“孔明既然走了,就不那么容易请回来咯。”
“那,那元直与我同去?”
“我说是不容易,不是说他不会回来。而且……”
“元直有话快直说!”
“孔明那小子,做事之前必会深思熟虑,一旦认准的事情,是很少变更的。当初他既然选择了出仕主公您,说明玄德公正是他心目中的明主!所以,”元直说到这里,突然收起了嬉笑的神色,目光中含了一种别样的庄重,“主公,不要再让他失望了,也不要再让天下失望了。”
很多年后,我向孔明谈起与元直的这段对话,孔明抱膝侧了头看我,但笑而不答,当其时,我才猛然醒悟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