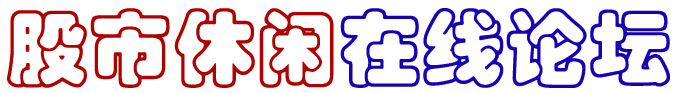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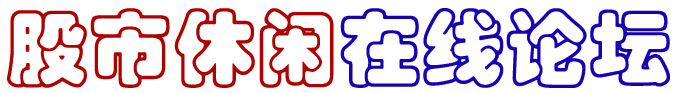
|
|
|
||||
|
第一,这不是俺写的。 第二,作者是谁想不起来了。 第三,仿佛是在龙鸣发过。龙鸣已经挂了。 第四,这是篇虐文应该。 题目叫《无题》 |
|||||
| 编辑 收藏 举报 主题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“怨我么,孔明?” 衰老的皇帝问跪在御榻前的丞相道。 榻前燃着的一盏孤灯昏黄的微光洒在丞相沉静的面孔上,借助这灯光,皇帝看到丞相微微蹙着眉,好像是在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此刻,一阵带着雨味的风从半开的窗里灌进了内殿,烛火摇摇欲灭,丞相的面孔霎时间变得模糊起来。皇帝望着这个朝夕相对了二十年的人,感慨万分地想道:“对我而言,真实的他似乎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。” 他伸出双臂将孔明打横抱起,将他放到卧榻之上。一面去解自己的衣袍,一面分开孔明的双腿。这样暴露在他眼前,孔明似乎感到有些羞耻,扭过头去,闭上了双眼。刘备对这轻微的抗拒报之以冷笑,他跪坐在那张开的双腿之间,揉搓着军师的下身,一面舔咬着双腿内侧敏感的肌肤。不到片刻,他就感到手中肿胀起来,被挑逗着的军师忍不住从唇间泄出一声低吟,这声音像是在刘备身体里燃着了一把火,他继续着手里的动作,另一只在孔明身体上到处游移的手伸向他的臀瓣。刘备的手指缓缓地插了进去,慢慢地搅动着,那一阵阵低靡的呻吟声霎时间转为一声惊叫,刘备压住了那副似乎要弹起来的身躯,继续着他的动作,将第二根,第三根手指插了进去。军师在他身下猛地一抖,刘备只感到掌心喷涌出一股灼热的液体。军师的腰身落回了榻上,无力地喘息着。刘备满意地蘸了些液体在手指上,在军师的后穴上涂抹着,然后将他的腿抬高些,一挺身,近入了军师的身体。“这个人竟是这么纤细么?”刘备托着军师的腰身,一面动着一面抚摸着,“仿佛稍一用力就会折断”,这从未见过的软弱模样使得刘备感到一种从未体会到的甜美,他托起孔明的背,让他在自己的双腿间坐直,一面气喘吁吁地命令道:“睁开眼,看着我。”孔明微微睁开了双眼,刘备半带恶意地问他道:“这样与我肌肤相亲,军师觉得羞耻么?”不等答话,他便堵住了孔明的口,掠夺着他销魂的呻吟,粗暴的吻使得军师一时间透不过气来,几乎晕厥过去,那被侵入的甬道因此缠紧了刘备的下身,发出甜美的摩擦声。刘备此刻再也无法保持任何节制,越来越用力地冲击着怀中那个单薄的躯体,疼痛之中,军师的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肩膀,“对,就这样,”刘备在孔明耳边低语道,一面用力地抽插着,交合之处渗出了一片殷红,孔明痛出了一额的冷汗,呻吟着向后仰去。两人的身体猛地颤动了一下,刘备在军师的身体里彻底地释放了出来。孔明重重地落到卧榻之上,两颊的红晕褪成一片苍白。刘备也精疲力竭地倒在了他身边。两个人一动不动地躺了片刻,刘备伸臂将孔明揽在怀里,他也不出声,任由他摆布。刘备吻着他的发稍,一只手摩挲着尚沾着灼热液体的双腿内侧,问道:“在我之前,又有谁享用过这身子呢?” 刘备见此情景,不由得冷笑了起来,他托住军师的下巴,对他道:“专心些,要是你的心神现在就飞到江东去了,我可就不知道这身子能否叫我满意了。”说罢,他一把将孔明推倒在榻上,没有任何前戏,就插进了他的身体。柔嫩的内壁刚刚停止流血,这一下硬生生的插入,痛得孔明叫了起来。刘备压着他的背,一面舔着他的耳垂,一面轻声说,“要想拒绝的话就说出来,当然,那样的话,你那个复兴汉室的梦想……”军师没有回答,痉挛的手指抓紧了铺在榻上的锦衾,这一次他咬住牙关,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刘备几乎折腾到天明才住手,看看怀里的军师,已是半昏厥过去。刘备将他头枕在自己的臂弯里,问道:“怨我么?”孔明紧闭着双目,什么也没有回答。刘备长吁了口气,轻轻抚拍着他的背,道:“以后我会温柔一点,来日方长呢,军师。” “主公要保重身体才是”有一次他对这过于频繁的肌肤之亲小心的提出了一句抗议,他的回答是狠狠地要他,做得他第二天清晨几乎起不来床。看着他白皙的胸膛和颈项上的点点瘀痕,他笑问道:“若是被属下看到这个,你该如何是好?”军师一面穿上严整的外袍,一面答道:“为臣之道,别人又有何可言?”这番回答竟有一种凛然不可冒犯的感觉。只有在将他赤身裸体体压在身下时,才能感到自己是他的主人,刘备恨恨地想,可是即使在那样的时刻,他心里装着些什么自己还是不能主宰。 而此刻,他心里正是装满了这种恨。他挖苦地对丞相说:“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 丞相抬起头望着他,皇帝一时间有些怀疑是否是昏暗的灯光使他产生了错觉,他的丞相的面颊上流淌着两道泪水,这个天在头顶塌下来都不会皱一皱眉头的男人在哭?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,愣愣地望着丞相。 “陛下以为”丞相的声音颤抖而哽咽“臣是为了什么跟随陛下这许多年……,在臣心里,汉室江山,天下苍生是重,可陛下,并不比这些轻啊,也许,就因为这是陛下的汉室江山,亮才有九死而不悔的勇气。二十年的岁月,竟换不来一刻的心意相通么?” 皇帝费力地支起身体,伸手去擦丞相满脸的泪水,滚热的泪水,烫得他的心不住地颤抖。自己的面孔何时被濡湿竟也不知道,皇帝抓住丞相的手,道:“朕糊涂啊。孔明,朕这一生,是负了你了,你怨朕么?” 丞相沾满泪水的面孔上展露出一丝微笑,“不,不怨” 皇帝望着他深邃的眼眸,好似要将这眼眸烙在自己的眼中,问道:“生已负君,死后可否与朕相随?生时虽得同衾,却辜负了你一片苦心, 丞相百年之后,可否与朕同穴?” 丞相含着泪答道:“臣当然愿意,可是,天命如何,尚未可知。” 皇帝听了这回答,眼中的光芒渐渐暗了下去,是啊,天命有时残酷得如此玄妙,发觉是竟是欲哭无泪。 十二年后,诸葛丞相病逝于五丈原军中,葬于距昭烈陵千里之遥的定军山。 ---此回复由王梦思明在2013-11-20 21:39:37编辑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我擦,这么渣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这个主公好渣的说,竟然这样的对军师,军师居然还这么的忠心于主公?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怪不得题目叫无题,真的是无题啊。除了那段字母情节,不晓得作者想表达什么。刘小备发什么羊角风?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我無言了。。。。。。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吾靠了,渣攻贱(弱)受,代入不了玄亮。有木有忠犬温柔攻女王傲娇受滴玄亮文推荐个?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我想這裡的主公心裡有些沒自信吧!因為對於得到了孔明這樣的人才,他的心裡愛、卻好像不踏實, 因為他怕,除了大業外...這個人心裡到底是怎樣看他、到底愛不愛他?!他只想將那個人佔為己有,心裡只有他,心中衍生了許多的情緒最後還是有些變了調,終至白帝城悲劇,還有最後的遺憾... 感謝夢姐的分享~^^
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这个好像是刘备怀疑亮和周瑜有一腿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好狗血。。。渣攻贝贝。。。以及贝贝哪有病危的样子。。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这篇。。。貌似看过,当时好像只有图片格式的,感觉眼花就没仔细看。。。结果现在还是看不下去。。。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看標題我還以為是夢大七年前寫的文 那個興奮啊 夢大你貼點自己寫的行不行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劉小備的醋勁挺大的....這大概也是因為年齡差異大,在老夫少妻來講常常較老的那個都是會比較沒安全感和疑神疑鬼的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啧啧,我还以为是清水……没想到这么香艳……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刘备怀疑亮亮和嘟嘟有一腿时很虐,但是结尾更虐啊,就不能改成两个人死后被人共同祭奠于武侯祠吗,刘小贝主动做了上门女婿……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嗯。。。一看就不是你写的。。。话说你写过H咩~ 刘备啊。。我怀疑你和诸葛亮有一腿是不是真的???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前面看着看着羞涩了,后面看着看着哭了.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太渣了 军师造孽啊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这个文以前看过,喜欢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回一个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渣攻....亮性子软了些,不甚喜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又被梦姐虐到了,一种身心剧疲啊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额,好吧。。。回避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渣攻备!还敢对亮亮用强!心疼亮亮啊TUT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
这个主公好渣啊 |
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龙鸣?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虽然这里的刘备有点渣,但是感情的把握和描写真棒,心痛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为啥丞相这么软弱啊=-=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天啦~~主公是要逆天啦,太邪魅了,亮亮好一副受样。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
|
|
|
||||
| 渣備啊……心疼亮亮,不過我愛吃肉! | |||||
| 编辑 回复此楼 举报 帖子管理 | |||||